就在諸多銀行自營消費貸利率迭創新低之際,定價趨于36%的高息網貸產品在中小平臺展現出擴張之勢。雖然這些網貸平臺最后的放款人可能是銀行、消金公司、信托公司、小貸公司等持牌金融機構,但有一方重要參與者不可忽視——充當助貸兜底角色的融資擔保公司。
“雖然融資擔保公司不是網貸里的必要角色,但是在助貸模式下,一般都會有融擔公司提供信貸增信,如代償擔保、風險分擔等。”一位資深業內人士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在大中型銀行、頭部平臺“掐尖”優質信貸客群背景下,一些持牌金融機構通過助貸平臺打開量價空間,瞄準高定價的下沉資產。
記者調研了解到,通過引入兩家融擔公司拆分定價從而繞開24%的利率定價上限要求的“雙融擔”操作正在行業內發酵。可以將這種操作簡單理解為,將36%的息費設置拆分為兩部分,分別通過不同的融資擔保主體實現,體現在客戶層面,就是需承擔融資擔保費以及融資擔保咨詢服務費。專家認為,這加大了借款人的債務脆弱性,表面上雖然分散了風險,實則形成復雜的擔保鏈條,可能減弱金融機構自主風控動力,導致風險向擔保體系過度集中。
無處不在的網貸入口
打開手機,越來越多的消費場景App接入網貸入口;應用商店里花樣繁多的專門分期、貸款類App,以及不能通過應用商店上架審核、需“定向下載”、主打資金周轉旗號的App無處不在,不禁讓人感嘆,真是“各種App都想借錢給你花”!
以消費場景App嵌入貸款入口普及為例,記者發現,不管是電商、短視頻、音樂類App,還是外賣、出行、美顏相機類App,都少不了網貸或助貸業務。蘇商銀行特約研究員薛洪言認為,電商、出行、生活服務等平臺通過內置信貸產品,將用戶行為數據轉化為授信依據,降低了借貸門檻,實現了信貸產品的普惠化。
冠苕咨詢創始人、資深金融監管政策專家周毅欽也表示,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金融消費者在日常消費場景中可快速獲得貸款服務,滿足了即時消費需求。而一些平臺擁有龐大的用戶群體和豐富的消費場景,通過接入貸款業務,能夠將流量轉化為經濟效益。
同時,記者搜索發現,應用商店和微信小程序中分期、貸款、資金周轉類的產品也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繚亂。
“這是平臺流量變現與消費者需求的雙向驅動所致。”周毅欽說,助貸平臺數量增多,表明市場對金融貸款服務的需求旺盛,尤其是在傳統金融機構覆蓋不足的領域,助貸平臺和助貸機構提供了更低的借錢門檻和更高的貸款可得性。
觀察一眾網貸產品宣傳頁面可以發現,不少平臺在提示最高利率上限時通常會提及24%或者36%。多位業內人士表示,一般認為,24%是法律強制保護的利率上限,36%是法律認定的高利貸紅線。
“前兩年,頭部助貸平臺對24%-36%的高息資產做了大力度壓降,目前定價基本限定在24%以下。而一些中尾部的助貸平臺定價趨于36%的高息網貸產品還在擴張。”北京一位資深助貸人士表示。
對于涉及持牌金融機構參與的網貸平臺,海潤天睿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岳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持有金融牌照的平臺屬于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審批的金融機構,其借貸糾紛不適用民間借貸利率上限的規定,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的規定,其貸款利率上限(包括利息、復利、罰息、違約金和其他費用)可以超過24%,但是如果主張的費用顯著背離實際損失,則超過24%的部分法院不會支持。
“平臺做36%定價的資產是在打擦邊球。”岳強說,平臺若是以超過36%的實際年利率實施非法放貸行為,則可能涉嫌非法經營犯罪。
高息費背后的融擔身影
金融機構信貸投放遵循差異化定價邏輯。上海一位資深信托業人士告訴記者,客群質量決定利率高低,更為下沉的平臺,其利率普遍偏高。“網貸客戶池內一部分是銀行的信用白戶,這部分人由于缺乏信用記錄或者征信欠佳,很難直接獲得銀行的信用類貸款,于是對網貸產生了需求,對應的利率定價也相對高些。”
某頭部助貸平臺人士告訴記者:“網貸背后有一類重要的主體,就是融資擔保公司,可將其理解為收風險撥備金的角色。比如,某地方性銀行與助貸平臺的合作模式是助貸,那么銀行就會要求助貸平臺找一家融擔公司去收風險融資擔保費。”
業內人士介紹,融資擔保公司常常充當助貸平臺的風險兜底角色,有合規性背書的作用,也能提高助貸業務鏈條的利潤水平,變相突破年化貸款利率上限。
“網貸業務不是必須要有融擔公司。借貸平臺直接放貸,法律并未強制要求引入融擔公司。融擔公司的核心作用是提供增信服務,如代償擔保、風險分擔,這一角色的出現是基于市場選擇而非法律強制。”岳強說,“網貸存在融擔公司角色,是借貸平臺為了轉移風險、最大限度保障自身利益的選擇。如果借款人還不上錢,平臺可以主張融擔公司替借款人還款。之后,融擔公司可以向借款人追償。”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助貸平臺的客戶被層層“掐尖”、篩選,36%的下沉資產又回歸到機構和平臺視野之內。在高息產品中,“雙融擔”模式頗為流行。在該模式下,息費設置為監管紅線內的含擔保費的年化利率加額外的融資擔保咨詢服務費。于資金方而言,這種做法可將業務合規下探,在信用風險走高情況下,通過高定價獲取高收益,對沖壞賬減值損失。
“‘雙融擔’從字面理解,就是將36%的定價拆分成兩部分,分別與兩家融資擔保主體合作,息費設置為24%以下和以上兩部分:24%以下部分設計為‘資金方利息+融資擔保費’,以上部分設計為融資擔保咨詢服務費。”北京一家助貸平臺人士解釋。
薛洪言表示,這一模式通過引入兩家融資擔保公司拆分定價,繞開了24%的利率定價規定。從積極角度看,該模式在客觀上擴大了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尤其是為征信記錄不足的下沉客群提供了融資通道,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傳統金融機構服務盲區的難題。部分消費金融公司借助此模式拓展縣域市場,打通了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
“但該模式的合規性存在爭議,表面利率合規與實質成本高企的矛盾,既變相繞開了相關規定,也損害了消費者權益,特別是對收入波動較大的新市民、靈活就業群體,過高的資金成本將加劇其債務脆弱性。此外,‘雙融擔’模式表面上分散了風險,實則形成了復雜的擔保鏈條,可能減弱金融機構自主風控動力,導致風險向擔保體系過度集中。”薛洪言補充道。
警惕“一鍵借款”便利背后風險
多位在不同網貸平臺有過借款經歷的消費者對記者表示,往往是在還款的時候才發現有融資擔保費、融資擔保咨詢服務費等條目,而此前并不知情。在互聯網投訴平臺,收取高額擔保類費用成為投訴的重災區。有消費者反映,“擔保費比利息費還高”,借款四五千元,擔保費就有上千元,擔保費占本金的比例高達20%-30%。
在岳強看來,網貸融擔費用居高不下的原因包括:客群主要是征信不良或資質較差的借款人,為覆蓋壞賬損失和運營成本,平臺傾向于通過擔保費、服務費等形式轉嫁風險;拆分利息名目,試圖規避法律對利率上限的直接約束;目前法律對擔保費、服務費的收取標準缺乏明確上限。
岳強表示,如果相關合同明確約定、服務實質對等且自愿同意、綜合成本不超法定上限,資質與流程合規,一般是合法合規的;如果存在陰陽合同、隱瞞收費與欺詐誘導、綜合成本突破利率紅線,或者無擔保資質的平臺自行收取“擔保費”、未經借款人授權通過第三方支付平臺自動扣劃費用等,屬于不合法合規的行為。
專家認為,融擔增信下的助貸,雖然為普惠金融打開了新路徑,但需在用戶體驗、風險隔離、消費者保護之間找到平衡點。
薛洪言表示,部分助貸平臺會通過默認勾選分期選項、弱化利率提示等設計,影響消費者知情權,存在過度營銷隱患。場景方與金融機構的合作機制仍需規范,部分助貸機構在客戶篩選、風險共擔等環節存在權責模糊,需要建立更清晰的合作邊界,確保金融機構獨立承擔核心風控職責。
“從規范的角度看,應堅持實質重于形式,明確要求金融機構承擔實際利率披露主體責任,將擔保費、服務費等所有成本納入APR(年化綜合成本)計算范疇,消除變相高利貸的土壤,更好保護借款人的合法權益。”薛洪言說。
周毅欽表示,部分平臺可能存在誘導用戶借貸、過度營銷等問題,增加了用戶的債務風險。部分機構可能存在風控不嚴、利率過高等問題,甚至一些網貸機構存在“線上線下兩本賬”故意繞開監管的情況。因此,需要金融監管部門繼續加強對這些平臺的監管,從源頭上對過度借貸、誘導宣傳、風險揭示不足、個人信息泄露等違法違規行為進行打擊。同時,平臺也應加強自律,確保貸款產品的透明性和合規性,保護好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關于網貸背后的信息安全問題,岳強提醒,金融消費者在享受各平臺“一鍵借款”便利時,需保持清醒認知。比如,仔細查看用戶須知,收集個人信息的范圍和用途,特別注意是否授權給第三方使用,警惕過度索權行為;遭遇信息濫用時,金融消費者可進行投訴或提起民事訴訟索賠。金融機構與助貸平臺在開展此類業務時,需要將數據收集最小化,避免超范圍、過度收集;將數據使用透明化,公開數據收集使用詳情;將流程合規合法化,避免強制、不正當收集和違規使用;將數據存儲安全化,進行數據脫敏與加密、使用權限動態管控等。
本文鏈接:http://www.020gz.com.cn/news-9-66919-0.html揭開助貸兜底面紗 窺見息費高筑背后擔保鏈條
聲明:本網頁內容由互聯網博主自發貢獻,不代表本站觀點,本站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天上不會到餡餅,請大家謹防詐騙!若有侵權等問題請及時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在第一時間刪除處理。

點擊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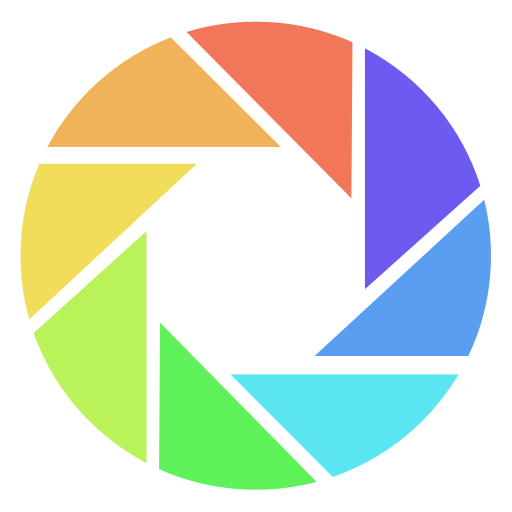 朋友圈
朋友圈

點擊瀏覽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 ”按鈕
”按鈕

點擊右上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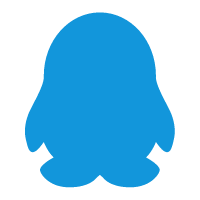 QQ
QQ

點擊瀏覽器下方“ ”分享QQ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
”分享QQ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 ”按鈕
”按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