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西北瀕危語言“留像續音”
——蘭州大學語言接觸研究團隊“冷門”路上守“絕學”
光明日報記者尚杰王冰雅光明日報通訊員魏淵博
“這些詞語就像草原上的風,一吹就散了。”在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牧民帳篷里傳出一段沙啞的吟唱———保安族老人馬占海正用保安語唱著流傳百年的歌謠。
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敏春芳坐在毛氈上,手中的錄音筆緊貼在老人唇邊,生怕漏掉一個音節。不久后,這個被稱為保安族最后“活字典”的老人離世,帶走了37個古波斯語借詞———這些詞語曾用于描述祆教祭祀儀式中的星象方位,如今只剩下筆記本上潦草的拉丁字母轉寫。
2024年年末,敏春芳帶領蘭州大學語言接觸研究團隊以“語言接觸視域下西北民族地區瀕危和接觸語言研究”項目入選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成為全國24個團隊獲批項目之一。
與時間賽跑,記錄瀕危語言
語言接觸研究是語言學領域的一個重要分支。敏春芳從2012年開始,將主要精力投向西北民族地區漢語方言與少數民族語言的接觸研究,并組建了語言接觸研究團隊。
“西北地區是語言資源的富礦,也是語言接觸研究的‘自然走廊’。”在敏春芳看來,這里聚居著漢、藏、回、撒拉等50多個民族,雙語或多語現象比比皆是,比如“一家人說三四種方言”“一條街東西南北不同語言”等現象普遍存在,形成了獨具地域特色的語言區域特征。
然而,現代化的浪潮正在加速地區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的消亡,且消亡速度比人們想象中的還要更快。
在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縣的尕楞鄉,24歲的撒拉族青年韓海明熟練地刷著短視頻。手機畫面上夾雜著漢語和撒拉語的“雙語彈幕”從他指尖劃過。“我爺爺能唱300首撒拉族民歌,但我連30首都記不全。”他苦笑著對調研團隊說。
敏春芳和她的團隊調研發現,撒拉語使用人口從20世紀50年代的12萬減少到如今的不足7萬,青少年群體中熟練使用者僅占15%。古老的“駱駝商隊”“羊毛搟氈”等游牧相關的詞語,正被“直播帶貨”“新能源汽車”等現代漢語詞所取代。
2024年暑期,敏春芳帶著團隊奔走在臨夏州積石山保安族東鄉族撒拉族自治縣、張掖市肅南裕固族自治縣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縣,對東鄉族的東鄉語、保安族的保安語、裕固族的東部裕固語和西部裕固語以及這些地方存在的“接觸性語言”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考察。最終,團隊帶回的筆記本上,記錄了3000多條東鄉語、保安語詞,其中大約40%的內容被紅筆標注“正在瀕危”“瀕危”。
“對沒有文字的語言而言,一位老人的去世,就可能讓幾十個詞永遠消失。”敏春芳說,“我們必須和時間賽跑,為這些詞語留下痕跡。”
用現代技術手段,為語言繪制“心電圖”
對于采集回來的語言素材,團隊并非一放了之,而是運用現代技術手段,如語料庫分析、計算語言學、人工智能等,對語言接觸現象進行定量和定性研究,來提高研究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敏春芳團隊建成了國內首個西北瀕危語言動態語料庫。在團隊成員向記者展示的語料庫中,一首《月光光》的音頻波形圖上,密密麻麻地標注著阿爾泰語系聲調標記,如同為語言繪制“心電圖”。整個語料庫內,28萬條語音數據、1900小時影像記錄和43種語言的語法矩陣正為文明續寫著最原始的基因編碼。
在敏春芳看來,冷門研究必須打破學科壁壘,才能促進研究的深入與拓展。她常把歷史比較語言學、民族社會學和生命遺傳科學比喻成破解瀕危語言和接觸語言密碼的“三把鑰匙”,只有與這些學科結合起來,才能將民族語言的研究引向深入。
敏春芳認為,語言中蘊含著大量的信息,能夠為破解諸多歷史謎團提供佐證。比如,通過團隊的研究發現,甘青河湟地區的漢語方言雖屬漢藏語系,卻在語序、格標記上與阿爾泰語高度趨同。“這不是基因傳承,而是千年交融的印記。”
扎實的野外調研和科學的研究方法讓敏春芳和她的團隊收獲滿滿。近10年來,團隊發表了60余篇論文,出版7部學術著作,研究成果受到國際語言學界的關注。法國國家科學院東亞語言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著名漢學家羅端曾表示,該團隊“為歐亞語言接觸研究提供了新范式”,為全球語言接觸研究提供了“中國樣本”。
“國際學界曾認為漢語是‘孤島型語言’,而我們的成果證明了漢語的開放性。”敏春芳欣慰地說。
冷門不冷,培養絕學研究“多面手”
和其他冷門絕學領域類似,瀕危語言和接觸語言研究也存在人才斷層的難題。對于如何激發學生興趣,敏春芳有著獨特的方法。
她把學生帶到祁連山牧場的高坡上。夕陽西下時,他們打開錄音設備,遠處傳來裕固族牧人用古突厥語吟唱的《遷徙長調》,聲波在監測儀的屏幕上跳動成連綿的山脈。“這是‘風’的聲音,在裕固語里,它叫‘khara’……”在這一場景中,她為學生解讀古突厥語;
她把學生帶到哈薩克斯坦的“陜西村”。東干族老人黑牙子·張用清代陜甘方言吟唱的《五更調》被團隊錄入“東干語數字基因庫”,其過程也記錄下了這一“19世紀西北方言活化石”的消亡;
她還帶學生去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七市一縣調查漢語方言,也去臨夏回族自治州東鄉縣的24個鄉鎮調查東鄉語和東鄉漢語,還到青海祁連山麓調查“托茂人”的語言……
“只有讓學生們在研究過程中感到有興趣、有歷練、有收獲,才能讓他們堅持下去。”敏春芳說,她鼓勵學生更多地參與跨學科、跨區域、跨語言的國際合作與交流,廣泛涉獵、兼通古今、合璧中西,成為一個語言學研究的“多面手”,在跨學科合作與國際交流中,讓冷門不冷,絕學有續。
《光明日報》(2025年03月25日09版)
本文鏈接:http://www.020gz.com.cn/news-3-604-0.html為西北瀕危語言“留像續音”
聲明:本網頁內容由互聯網博主自發貢獻,不代表本站觀點,本站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天上不會到餡餅,請大家謹防詐騙!若有侵權等問題請及時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在第一時間刪除處理。
上一篇:到新疆赴一場“春天之約”

點擊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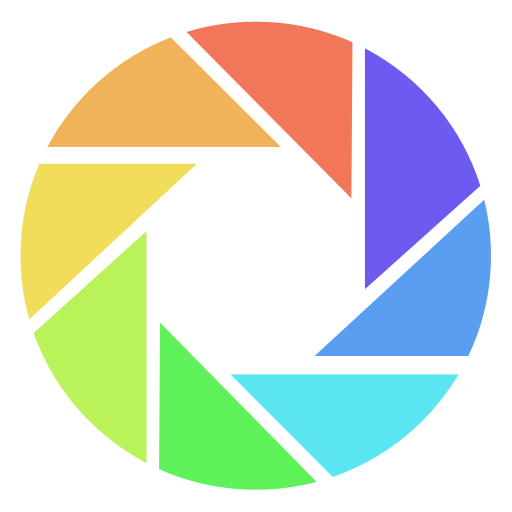 朋友圈
朋友圈

點擊瀏覽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 ”按鈕
”按鈕

點擊右上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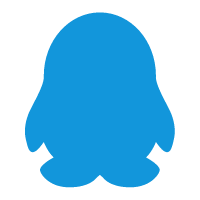 QQ
QQ

點擊瀏覽器下方“ ”分享QQ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
”分享QQ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 ”按鈕
”按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