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保護團隊在進行數字化采集。
敦煌研究院供圖
2006年,敦煌研究院組建了以青年專業技術人員為主的文物數字化保護團隊。19年來,一批批年輕人迎難而上,接續努力,開展文物數字化技術研究及敦煌石窟的數字化信息采集與轉化利用,助力實現文物信息資源“永久保存、永續利用”。
近日,本報記者走近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保護團隊,在光影世界里傾聽石窟里的千年古韻,感受保護團隊矢志創新、協作攻關、接力傳承的奮斗故事。
——編者
輕敲鼓槌、打開手電、拉近壁畫……伴隨神秘悠揚的古樂,體驗者僅靠一只手柄,就能在不到1平方米的體驗臺上了解敦煌莫高窟第285窟的前世今生。
甘肅省敦煌市莫高窟窟區,“尋境敦煌——數字敦煌沉浸展”體驗展館就坐落于此。展館里,韓雪在為體驗者穿戴VR(虛擬現實)體驗設備。作為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保護團隊的成員,她全程參與了“尋境敦煌數字敦煌虛擬現實深度漫游·莫高窟第285窟項目”。
2006年,敦煌研究院專門組建了以青年專業技術人員為主的文物數字化保護團隊,開啟自主實施數字化保護的歷程。19年來,這支團隊建立了一套科學規范的技術體系,書寫了一個個敦煌“永久保存、永續利用”的故事。
創新,讓洞窟走向公眾
在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是現存最早的有明確建窟紀年的石窟。為保護文物,第285窟現已不再常規開放。那么,游客還有可能體會身在洞窟的感覺嗎?
現在,除了在莫高窟景區進行VR體驗,人們還可以登錄“數字敦煌”網頁或“數字敦煌沉浸展”小程序,線上探索第285窟的細節。
“如何拉近敦煌與公眾之間的距離,是數字化團隊一直在鉆研的課題。”韓雪介紹,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保護團隊現有110人,包含35歲以下青年67人,來自計算機、攝影、藝術設計、動漫等多個專業,他們每個人都在不斷探索本專業與敦煌之間的連接……
2022年底,團隊啟動了“尋境敦煌”項目的籌備工作。尋求技術合作方、修改設計思路、實施實體和虛擬項目……“相比于制作數字展廳,打造沉浸式體驗對細節要求更高,有時候僅后期渲染一次就得兩三個月。”韓雪說,“大家發揮各自專業特長,歷經一年多才正式發布成果。”
在蘭州大學秦嶺堂的大廳里,還有一座特殊的“第285窟”。它全稱“高保真原大數字化仿真洞窟莫高窟第285窟”,長寬各近7米,高近5米,一比一還原第285窟,師生們可以在其中體驗考古的真實情景。
“一次創新,給師生帶來新的教學方式,也為我們積累了寶貴的經驗。”2022年項目啟動以來,團隊成員段雅潔一直參與其中,經歷了不少挑戰。
比如,在粘貼壁畫環節,為了更好地還原原窟的質感和色彩,段雅潔采用宣紙噴繪壁畫的方式,難點在于貼合性、牢固性。同時,窟體是不規則形狀,她和同事站在幾米高的腳手架上,先加固窟體,再小心翼翼地一張張貼上去,慢慢摸索不同部位的特點,在每個細微處都做好配合。“這個環節就幾乎占了整個施工期的一半。”段雅潔說。
開設“絲綢之路上的敦煌”數字展覽,制作162個洞窟的全景漫游節目,推出“敦煌壁畫藝術精品高校公益巡展”……近些年,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保護團隊不斷創新,讓瑰麗的壁畫、神秘的洞窟走出大漠,促成公眾與敦煌的一次次相遇。
協作,讓壁畫變成數據
數字化成果碩果累累,海量素材從何而來?
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保護團隊有個傳統,新入職的職工必須先到洞窟里熟悉基礎知識。10年前,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韓雪認識了數字化保護領域的前輩余生吉。
遇到超大型壁畫,怎么才能平穩采集?遇到設備難入的狹小空間,如何保證完整采集?遇到超高彩塑、凹凸不平的壁面,怎么樣減少畸變?……“每面對一個新壁面,都是不同的挑戰。”余生吉說。
20世紀80年代末,余生吉入職敦煌研究院攝影錄像部,負責部分洞窟壁畫的圖像收集。面對精密儀器太少、成熟技術欠缺等短板,余生吉和同事們解決了一個個難題——自主研發柔光箱,讓照片更具質感;創新設計軌道、攝影架,讓拍攝能夠適應不同洞窟形狀;不斷提升圖像采集精度,滿足更多數字化場景需要……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保護團隊已完成敦煌295個洞窟的數據采集,壁畫采集面積約2.8萬平方米。
和數字化采集團隊一起在洞窟里忙碌的,往往還有圖像處理團隊。安慧莉就是其中之一,她把采集到的圖像拼接起來、定位校正,最終成品要做到“天衣無縫、色彩自然”。
安慧莉說,采集一個壁面,拍出的素材最少也有幾百張,最多的達到上萬張。壁畫的體量、形制不同,采集到的圖像曲率變化有差別,因此拼接方法也各異。最初純手動拼接時,一天只能拼接3到5張。后來,團隊和科研院所合作,逐漸發展出“井字格”“魚骨架”等圖像處理方法,大大提高拼接效率和精準度。如今,圖像拼接的方法仍然在不斷創新,錯位、斷線、模糊等問題也能被準確發現并糾正。
現在,即使面對高近30米的大型洞窟,安慧莉和同事們也能從容應對,每人每天能拼接超過20張素材。
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保護團隊已完成對190余個洞窟的圖像拼接處理,三維重建45身彩塑、7處大遺址,數字化掃描5萬張歷史檔案底片。
接力,讓技術應用更廣
通過數字化,洞窟和壁畫穿越了時空、走出了大漠。但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保護團隊仍在接力傳承,讓數字化保護技術能在更多領域綻放光彩。
“彼之花容,同桂蘭而永茂”“絲路盛景,華服衣冠”……讀完封皮上的文字,打開內飾,幾枚花鈿躍然眼前。取下花鈿貼在眉尾、額心、鼻翼和嘴角,點上幾滴清水,一套五代時期的花鈿妝容很快就成形了。
此前,敦煌研究院的“敦煌花鈿賀卡系列產品”圈粉無數。花鈿的原型是榆林窟第19窟的涼國夫人形象,正是得益于數字化素材的精準獲取,這一美麗的形象才能進入當代人的生活。敦煌研究院文物數字化研究所副所長丁小勝介紹,近年來,基于數字化技術,首位數字敦煌文化大使伽瑤、“敦煌文創”數字藏品等文創項目一一上線,數字化保護技術的應用領域也逐漸拓展到洞窟之外。
連續3年,95后青年團隊成員熊業騰幾乎每天都會踏查窟區四周情況,地形特征、四季變化、降水記錄……各種信息都是研究對象。“周邊環境也是莫高窟文物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最終,我完成了一份關于莫高窟與周邊環境的影像紀實和研究報告,這離不開數字化技術的支撐。”熊業騰說。
現在,數字化保護技術走得越來越遠——
在國內,團隊在戈壁和深山中采集、記錄和分析,不僅讓甘肅70多處巖畫有了“身份證”,還在新疆、西藏、陜西等地的18家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實施信息采集、數字復原等項目。在甘肅酒泉肅北蒙古族自治縣,團隊成員翻山越嶺5個多小時,找到刻在山頂石頭上的一只“鹿”;在蘭州永登縣魯土司衙門舊址,團隊成員改良采集角度,解決現有設備無法達到等問題……
在國外,團隊為國際文物保護工作提供中國方案。團隊派出6名青年技術人員前往緬甸,承擔了“援緬甸蒲甘他冰瑜寺修復項目壁畫保護信息提取技術合作項目”,取得良好效果。
在敦煌研究院的辦公區里,一座名為《青春》的雕像栩栩如生。雕像以“敦煌女兒”樊錦詩為原型,她身姿挺拔,向遠方凝望。數字化保護團隊每天都能看到這座雕像,激勵他們繼續努力。千年敦煌,煥發著永久的青春。
■記者手記
感受數字敦煌魅力
“敦,大也;煌,盛也。”塑像林立、壁畫連綿,延續千年的洞窟熠熠生輝。
技術更迭,矢志不渝,一代代青年傳承守護敦煌的使命。窟里的每個細節,都可能成為一道難題。他們傳承著前輩們的奉獻精神,勇于挑戰、攻堅克難,把數字化技術越做越新。
技術賦能,心懷遠志,一代代青年傳播璀璨的敦煌藝術。從資源庫到小程序,從參與式博物館到球幕電影,他們為敦煌文化想出新“玩法”,讓更多人感受敦煌的魅力。
現在,除了敦煌莫高窟,敦煌研究院還負責瓜州榆林窟、天水麥積山石窟等石窟的管理保護工作,對外交流研究也更加頻繁。面對愈發廣闊的舞臺,文物數字化保護團隊將繼續探索數字化技術,讓一座座藝術寶庫煥發數字化新光彩。
《人民日報》(2025年02月17日06版)
本文鏈接:http://www.020gz.com.cn/news-3-280-0.html一只手柄了解前世今生!19年來探千年石窟之秘
聲明:本網頁內容由互聯網博主自發貢獻,不代表本站觀點,本站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天上不會到餡餅,請大家謹防詐騙!若有侵權等問題請及時與本網聯系,我們將在第一時間刪除處理。

點擊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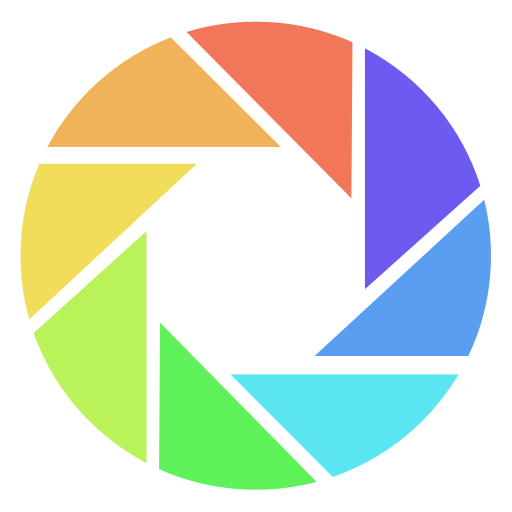 朋友圈
朋友圈

點擊瀏覽器下方“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
”分享微信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 ”按鈕
”按鈕

點擊右上角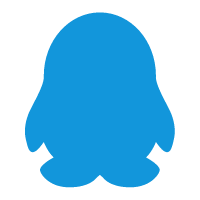 QQ
QQ

點擊瀏覽器下方“ ”分享QQ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
”分享QQ好友Safari瀏覽器請點擊“ ”按鈕
”按鈕
